□江少宾
认识张扬很多年了,我们既是同乡,又是同行,往来之间自带一份亲近感。那些年,他主持《安徽商报·橙周刊》,筹划了一个又一个热度很高的文化活动,在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的本土文化圈子里,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流量。他不止一次邀我采风,我都推辞了,近乎不通人情,他并没有因此心存芥蒂,见面时一如往日,老成持重的样子,云淡风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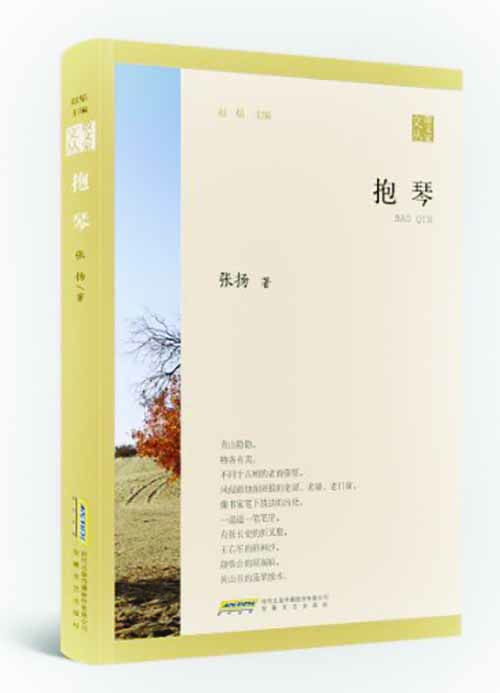
那些年,张扬是一个忙忙碌碌的活动策划人,我有时不免替他惋惜,传统媒体遭遇寒冬,他有目共睹的辛苦付出,既无法扭转业态大势,也无法改写个人命运。更让我惋惜的是,他已经无暇写字了,虽然偶尔也有文字见刊,但老实说,我读后印象都不深。这责任自然在我——我一向对“采风式写作”抱有成见,也一向认为,俗世过于喧嚣,而写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,关乎理想,也关乎灵魂,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,理应排除一切外部干扰,我手写我心。众所周知,写作是长跑,考验的不光是才华,还有体力、定力和毅力。半途而废,慢慢掉队的写作者太多了,跑着跑着,道路越来越窄,队员越来越少,我敬重那些一意孤行的人。
忽然就收到张扬的新著《抱琴》(“散文家文丛”,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),全书收录了四十篇短文,大体上说来,写的都是平常人、平常事、平常心,但平常中自有不平常处。这套丛书的主编赵焰先生有这样一个遴选标准:“文章以美为表,以真为骨,以趣为气,以好读和耐读为基本要求。”以我看,张扬的文章,当得起一个“真”字。何谓“真”?以我粗浅的理解,便是“修辞立其诚”。散文写作尤其需要“诚”,即以一颗虔诚之心,观自然,万物,众生。很多人的散文里都有一个“我”,“我”固然是我,但也不妨是他人,“我”,立其诚。散文写作自有其伦理,但捧着一颗心来,是散文写作的灵魂。
因为真,张扬的文章见情、见性,好读,也耐读。比如写杨绛,“杨先生愈老愈美愈纯,最终收起自己在人世间的脚印归去。槐聚槐散,人生的谢幕有早有迟,人生的悲欣有浅亦有深。”再如写大潜山房,“不同于古树的老而弥坚,风侵雨蚀而斑驳的老屋、老墙、老门窗,像书家笔下技法的出处,一道道一笔笔里,有张长史的折叉股,王右军的锥沙画,颜鲁公的屋漏痕,黄山谷的荡桨拨水。”字里行间彰显灵动之美,悠悠有古风。古风是中国文脉,是人情练达,是世事洞明。食古最怕不化,难在深入浅出。张扬行文,大体在深浅之间,行得稳,走得正,当真是文如其人——人不张扬,文也不张扬。人不张扬,自然是修为,文不张扬,则是智慧了。
张扬信而好古。他有较多的文字写到了香炉、珠玉、陶罐、旧信札、琉璃瓦……都是古旧之物,难得的是没有拘泥于考据,行文平白如话,掌故多雅趣,册页间浮动着漫漶的文明。我本俗人,不懂这些,只是好奇,一路读下来,竟也饶有兴味。这样的文章不是人人都能写的,需得有学识酿就的底子才行,张扬的文章因此立了起来,有了些许风姿。可不要小看了这个“立”字,很多人的文章看上去像模像样,其实徒有其表,身子骨整个是软的。当然,文无定法,这样的文章并不一定就不好,只是在我看来,这样的文章没有价值,至少价值不高。
散文易写而难工,它是一种藏不住人的文体,每个人的书写都是一面多棱镜,折射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。在这个层面上观照《抱琴》,我以为尚有部分篇章火候不足,成熟度不高,它们由“真”而来,又止于“真”。“真”只是散文的第一个境界,而散文的魅力,在于其博大而自由的体性。好在吾道不孤,我们一直在路上,《抱琴》让我看到了张扬的情怀和初心。假以时日,张扬一定能写出更有意味、更有底蕴的大作品。

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2246号
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2246号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