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章宪法
乡土题材的书写,一直有着不俗的市场表现,更有作品摘得文学大奖。相对于《旧山水》《大地的细节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回乡记》《细味人间》以及更早一点的《独语东北》等,魏振强先生的《村庄令》写出了又一种乡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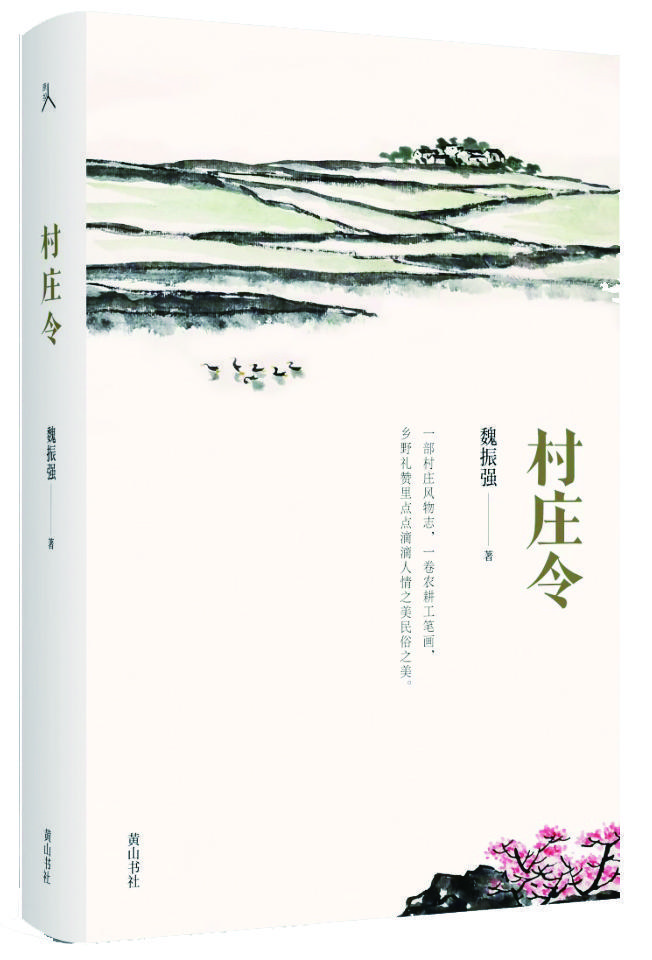
亟亟现代化的当代社会,乡村是最为迟缓甚至是晚熟的一块。《村庄令》的书写,大多在这一背景下展开:相依为命的外婆,逝于异乡的表弟,城中落户的玩伴,多以不同的方式离开原本的乡土;与作者之间有着无可名状情愫的村姑,长大后在村里开着农用车的发小,虽然始终生活在乡土,但不再重复昨天的故事,也无法回归旧时的情境。时代是一把刀,每个人的今生今世,都被分割成绝然不同的部分。山芋、甜瓜、西瓜、糖稀,由此成为意象。作者总有难以言说的深情在心中涌动,大脑中既不能删除,又无法“复盘”点点滴滴。
作者对乡土人和事的表达,完全是中国画似的散点透视。这种处理方式,灵活地拉近或推远描摹的对象,形成画面感的特写或留白。作者刻意写到表弟的葬礼,勾勒似曾熟悉的人:“我和宗文大哥说话的时候,一个壮壮实实的戴着鸭舌帽的男人给我递了一根烟,我接了,没说话。过了一会,那男人又走过来,给我递烟,问我:‘强子吧?’我看了又看,连蒙带猜:‘你是宗超二哥?’他说:‘是的,我们好多年没见了。’我说:‘快四十年了吧。’”这类文字没有绚丽的色彩,只有淡淡的墨痕,却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这个时代:时代的天翻地覆,只是毫不经意的流逝,成为纯粹的时间,不承载任何故事。而一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,就是没有故事。
哲学与文学,都在寻求时代的表达。哲学试图创造表达的“天花板”,文学试图穿越表达的“天花板”。韩少功先生评价《村庄令》“是一卷风物志,更有一颗自然心,复活了日月山川草木鱼虫,含蓄、质朴、纯净,平实的人间记忆难掩温情和力量,如一杯杯佳酿意味深长”。所谓的“复活”与“佳酿”,都是时间意义上的勾连与穿越,简单呈现从来都不是文学。
七十多年前,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说: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,乡下人离不了泥土,因为在乡下住,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。传统社会的乡村生活,基本上局限于步行一日往返的半径之内,也就是作者数次写到的父亲挑着稻箩穿行的距离。这是基于传统交通等自然条件下的自然选择,由此形成最基本的社交圈与文化圈,现代社会条件下不复存在。作者说“我像一个盲人,被他们领着”,“我印象中的绿油油的稻田现在正荒芜着。曾经的每一条田埂,甚至田埂上的每一个缺口的位置我都记得很清晰,但现在它们好像都消失了或者挪了位置”。
这个时代的与众不同,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时代,如同远望另一个时代。这种“飘移感”的抓取与表达,正是《村庄令》的敏锐之处。曾经的人,曾经的事,都不是浅浅的遇见,而是鬼神般的共振。这个时代作家有价值的书写,就是指间灌满时代的风,笔尖留下鬼与神。

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2246号
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2246号


